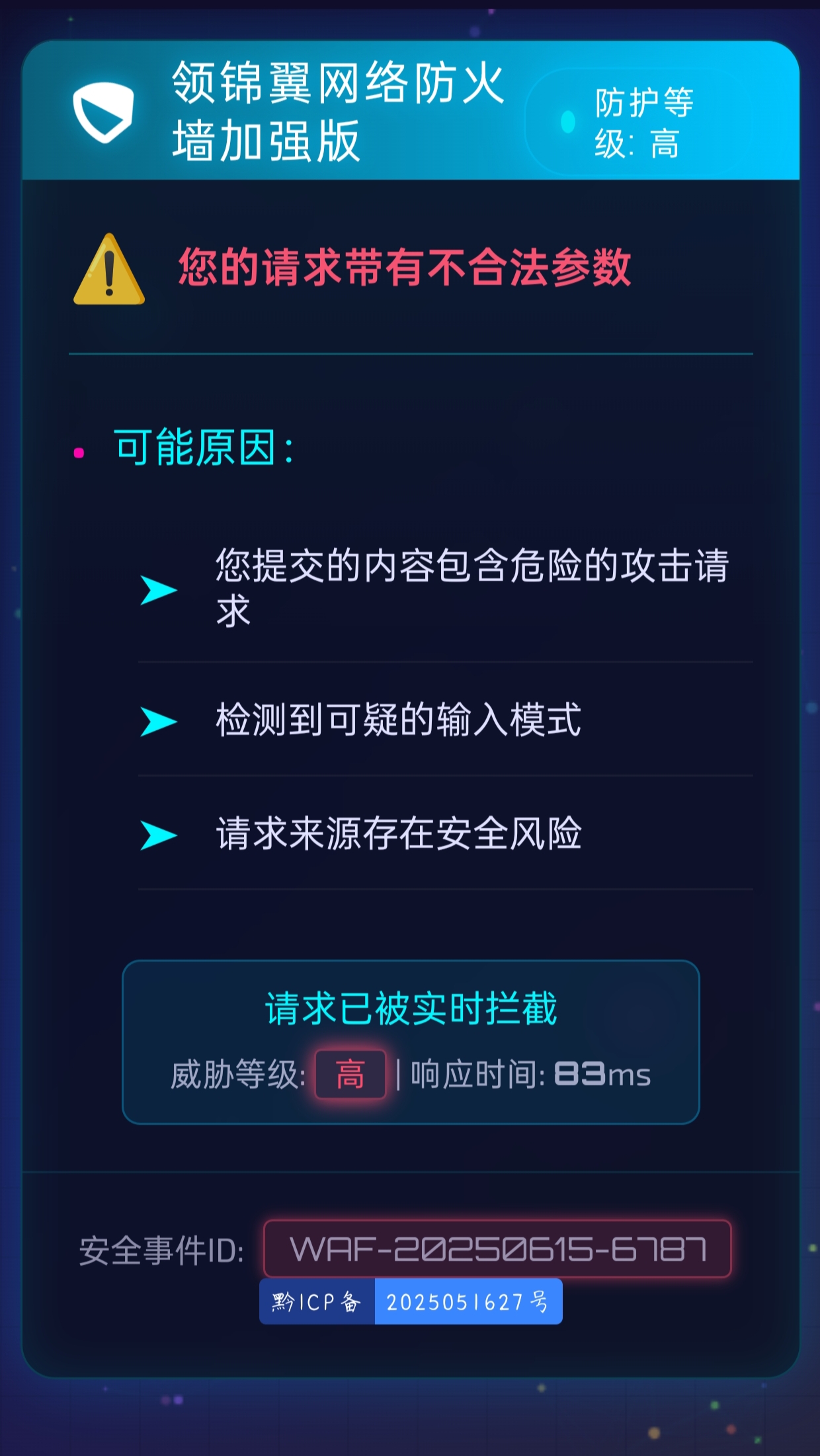老座钟的最后一声鸣响
林晚秋推开阁楼门时,积灰在光柱里翻滚成细小的星云。角落里那座红木座钟像位沉默的老者,铜制钟摆悬在半空,玻璃罩上的划痕里积着十年未动的尘埃。
“这钟还能走吗?”她伸手去擦玻璃,指腹立刻沾了层灰黑。母亲临终前攥着她的手说,阁楼里藏着能让时间慢下来的东西,当时她只当是老人的胡话。![图片[1] - 老座钟的最后一声鸣响 - 锦元博客|再续前缘之超凡境界 图片[1] - 老座钟的最后一声鸣响 - 锦元博客|再续前缘之超凡境界](/usr/uploads/2025/07/593150005.jpg)
楼下传来搬家公司的脚步声,地板在震动。这座住了二十八年的老房子明天就要易主,她是回来清理最后一批杂物的。座钟底座忽然发出轻微的“咔嗒”声,林晚秋吓了一跳,后退时踢到木箱,里面的旧相册摔出来,泛黄的照片散了一地。
最上面那张是十岁生日,她坐在蛋糕前,父亲正往她脸上抹奶油。照片里的座钟摆在客厅柜上,钟面指针指向下午三点十分。她记得那天父亲接了个电话就匆匆离开,再也没回来。后来母亲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,直到三年前整理遗物,才在保险单夹层里发现一张癌症晚期诊断书。
铜钟摆突然晃动起来,发出生锈的摩擦声。林晚秋凑近看,钟面指针竟开始逆时针转动,玻璃罩上的灰尘随着气流旋转,在她眼前幻化成雾气。当指针指向三点十分时,整座钟发出震耳的轰鸣,她被一股力量拽进白光里。
“晚秋,别碰电源!”
熟悉的声音让她猛地睁眼,父亲正举着吹风机站在浴室门口,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,腕上的旧手表闪着光。镜子里的女孩扎着羊角辫,鼻尖还沾着蛋糕奶油——是十岁生日那天。
她冲过去抱住父亲的腰,布料上有淡淡的烟草味和消毒水味。这个拥抱比记忆里消瘦许多,她才发现父亲的肩膀已经微微佝偻。
“怎么哭了?”父亲笑着擦掉她的眼泪,指尖冰凉,“不是盼着爸爸陪你去公园划船吗?”
林晚秋盯着他的眼睛,那些到了嘴边的话全堵在喉咙里。她知道这是座钟制造的幻觉,却舍不得戳破。公园里父亲陪她喂鸽子,看她荡秋千时笑得像个孩子,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,她偷偷数着父亲鬓角的白发,有七根。
暮色渐浓时,父亲口袋里的传呼机响了。他看了一眼,脸色忽然苍白,匆匆说要去单位加班。林晚秋拽住他的衣角,声音发颤:“爸,明天去医院看看吧,我同学的爸爸就是总咳嗽,后来……”
父亲愣住了,随即摸摸她的头:“傻孩子,爸爸身体好着呢。”他转身的瞬间,林晚秋看见他用手按住了胸口。
座钟的轰鸣再次响起,白光吞噬视野前,她听见父亲说:“晚秋要好好照顾妈妈。”
阁楼里的尘埃落回原处,钟摆恢复静止。林晚秋跪在地上,手里攥着那张父亲最后一次离家时穿的衬衫,领口还留着她偷偷绣的小太阳——那年她学了半个月刺绣,想在父亲节给他个惊喜。
楼下传来敲门声,中介带着新业主来看房。林晚秋把衬衫叠好放进木箱,最后看了眼座钟,玻璃罩上映出她泛红的眼睛。
“这座钟不搬走吗?”新业主好奇地问。
“留给房子吧,”林晚秋轻轻抚摸钟壳,“它在这里等了太久了。”
走出单元门时,手机收到母亲的短信:“梦见你爸了,他说在那边种了很多你爱吃的草莓。”林晚秋抬头,初夏的阳光穿过梧桐叶,在地上洒下跳动的光斑,像极了父亲当年陪她捉过的萤火虫。![图片[2] - 老座钟的最后一声鸣响 - 锦元博客|再续前缘之超凡境界 图片[2] - 老座钟的最后一声鸣响 - 锦元博客|再续前缘之超凡境界](/usr/uploads/2025/07/188158886.png)
街角的修表店挂着“停业清仓”的牌子,她忽然想起父亲的旧手表,也许该送去修修。有些时间不是用来忘记的,是要带着它,慢慢走向更远的地方。